崔保成
儿时,每逢腊月初八,老百姓便念叨“吃了腊八饭,忙把年来办”。临近春节,街上小娃子越发蹦蹦跳跳,盼着“过年 ”穿新衣,有好吃好玩的。大人们从娃子身旁走过,便会心境复杂地说上一句:“小娃子望过年,大人望种田啊”。
小城的人尽管没有“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的土地耕种,但种田是俗语、是劳作的代名词。大人们为儿时我们的温饱,艰辛地“种田”,“过年”对有些人户来说还真叫“年关”。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的父辈们年年岁岁的“望种田”,才有我们少儿们的“望过年”啊!
我生于一九五七年,记事的时候已是六十年代初。小城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机动车,少有几处两层的“洋楼”,冬日里的夜空连星光也不怎么闪烁。小城平常就是一种宁静、安详、日升月落。
有明清风格的街道一院落一院落地连着。青砖隔墙,小黑瓦房顶,低矮阁楼,门面大都是已显很陈旧的油漆木板。傍晚,各户掩映的木门内的堂屋桌上,朦朦地闪出一盏煤油灯的淡黄光亮。显点儿热闹的地方也只有县豫剧团和电影院。
腊月,如若下雪,小城的街道、小城的房顶、小城周边的群山素净的白茫茫一片。只有堵河清清地、静静地、缓缓地绕着小城,象丝带般流淌在雪的上面。城里没有梅花,周边的山上倒有不少盛开小黄花儿的很香的腊梅。因之大人们年年岁岁为温饱而操心着“种田”,也便没有“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浪漫文气,只是“过年”的味儿会越来越浓。
要“过年”了,母亲们会拿出平日舍不得用的布票扯点布,给娃子们做身新衣裳。会三五成群地聚在太阳下,纳着鞋底忙着做新鞋。大人们或自己或吩咐大孩子们拿着肉票去食品割些肉,拿粮本去买些白糖、粉丝、木耳等一些春节才供应的“副食品”。冷湫湫的天气,大人和孩子们多会在屋里围在烧煤的地炉子边,暖着脚,烘着手。
待到腊月二十几,家家都开始打扫阁楼屋架和角角落落的“杨尘”,扯下竹隔栅上年糊的发黄窟窿吧眼的旧报纸,再在两面糊上新报纸,极少讲究的人家用“皮纸”糊上。二十五六开始蒸合碗菜,有红肉、酥骨、肉丸子、糯米甜碗;蒸馍有肉包、菜包、糖包、油盐卷;然后就是炸绿豆丸子、麻叶、冻米花等。
那年腊月,可能我六七岁吧,其时父已病逝年余,母亲操持家务,大哥在乡下工作,嫂子和大姐在城里上班,侄儿尚幼。母亲虽大字不识一个,但却执着的让大哥大姐在解放前的时代,分别读了中学和师范。而我和大我三岁的小姐也在六七十年代读完了高中。
一早,邻居街坊家家拿出前几日在街上字摊上老先生那里买的毛笔写的对子,新华书店买的门神画、年画,贴在门口屋内,一下子显得喜气洋洋。
我知道我也有新衣裳,但要等到除夕洗澡后才换。小城的人家,按祖籍地的不同习俗,各家团年饭有夜半凌晨的,有早有午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吃团年饭前,全家聚在热气腾腾的大方桌旁,待坐在上席高椅子上的长辈一声“放炮”,门外便响起“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满街弥漫着硝烟的香味儿和一地红红的纸屑。
大哥也从乡下回来了,他算盘打的霹雳呱啦的,会记账,我儿时的印象就是一“先生”样儿。每年年前,他都会托人挑些年货回城,这时母亲的眼里便会闪现出一些欣慰和期盼。嫂子在集体饭店上班,但在家平时不做饭。大姐从大山里学校,别了教书,回城做了建筑工,真是“父命不可违”啊,也是一辈子不会做饭。
“过年”大都是母亲操办,中午的团年饭还没开。母亲从烧煤的高炉子上的鼎罐里,在熬的飘香的肉里,捞出一根猪尾巴递给我,我就拿着它倚在街门前的木板墙,啃着啃着,嘴角小手糊得尽是油。那香劲儿、那馋劲儿,那幸福,那被爱,任什么词汇也无以描述。
待到腊月30日晚上后,各街办,甚至郊区大队组织的“演玩艺儿”的,便一拨接一拨地来我家斜对面,县政府八字门的场地上,锣鼓家什叮呤咣啷一阵敲后,那蔑编纸糊的龙灯、狮子、毛驴、蚌壳、旱船……便开始活灵活现地舞了起来。在无电黑夜的晚上,虽没有大都市“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景象,却因众多孩童举着的燃着的蜡烛纸糊彩灯、喷向耍火龙的砖头花,使小城有了片片簇簇热闹地亮光。这“过年”一直要热闹到正月十六才算过完。
那时守岁,没有钟表,只有鸡鸣。“残腊即又尽,东风应渐闻。一霄犹几许,两岁欲平分。”第二天,正月初一,满街的红春联、彩门神,满街穿新衣嬉戏的娃子们,让人顿感焕然欢欣。
一眨眼,孩提、童蒙、弱冠、而立、不惑、知天命、花甲之年匆匆而过,时光流逝了六十五个春秋。“明日便为经岁客,昨朝犹是少年人。新正定数随年减,浮世维应百遍新。”
回望儿时,我是幸福的,过年是快乐的。
看当今,我还在坚持“种田”,快乐地“种田”。有时尽管有些“种田”的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艰辛波折,甚至某些个体会遇到委屈冤屈,更甚至感受严重不公,被践踏,遭受丑恶的“毒瘤”侵扰。但“种田”的整体是勃勃生机向前发展的。
我没有网络上流言过的“生在五十年代,赶上饿饭、赶上失学、赶上下乡、赶上待业、赶上计划生育、赶上下岗、赶上再唯文凭……”,那种悲天悯人的低落磨难哀怨。有的是经历和目睹了前无古人的新社会顽强地生长,波澜壮阔地意识与经济的变革,人民物质精神生活的逐渐富裕多彩,国家的日益强大……,这些不同发展时代的“确幸”感。
忽发幻想,我们不过是中观世界里生物普系里一芥末样片段,在无穷大远处的宇宙和无穷小微处的量子物质世界里,你还有什么悲欢?还有什么不能放下?……至少烛光渐暗的我。
我的少儿时代是幸福的,我的学生时代虽断续也是完整的,我的青年时代是努力的,我的中年时代是拼搏的,我的老年时代是无忧的。想起少年时读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回首往事,在“活着”时代的社会里,虽无毫厘“栋梁”,但作为“一砖一瓦”还算是没有“碌碌无为”!没有“悔恨”!
人生的价值也许不是用某个时点的多少金钱、多高地位和寿命长短来衡量,而是“种田”的“过程”是否持续努力。
回到腊月,回到“过年”,我为我生在当今的中国由衷地感到幸运幸福,常念党的伟大、赞美祖国的不断强大!
如今的“孩提”,不在是追逐“温饱”,不在感受“贫困”,不在是“望过年”。因为天天有钱能吃肉了,天天都有新衣裳穿了,一出生包裹的便是五光十色的信息时代,天天生活都像在“过年”。
为了康健我们克制吃肉,“父辈们”唯有“种田”的精神代代相传:这就是“勤奋!”。“种田”也不再是追求“温饱”,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空间里努力学习、更新知识、拓展思维、变异创新、拼搏前行。
你只要“春种一粒粟”,总会有希望“秋收万颗籽”的。
中华民族的整体,不正是在这众多的个体的努力中,得以发展、强大,生生不息,进而推动全人类的进步吗!
谁说我们不是生活在糖罐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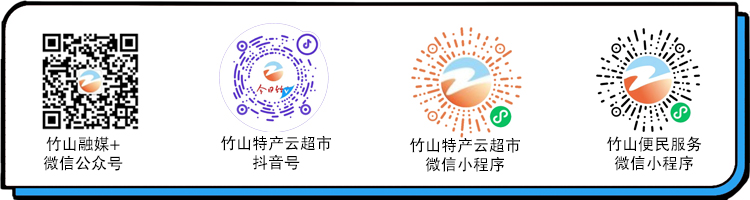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