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雅屏
电视剧《人世间》开播后,我几乎每天晚饭后、开播前都要去父母家坐坐,听他们谈谈这部电视剧,唠唠那个年代的悲欢离合,每一次的话题都让我感慨万千,心思沉重......父母不是局中人,是现实中的每一个平凡的人。听父母的诉说,我也感知了父母那代人的奋斗、成长和相濡以沫的温情,更感知了他们那代人对家庭的付出、善良正直、有情有义、坚韧担当的中国人形象。于是乎我就一此次冒出念头要写写父母的“人世间”。
我和我弟都是70年代初的人,我们和其他孩子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从出生都没有见过我们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我们睁开眼睛看到的世界就只有父母。我们幼时没有人帮忙带,母亲最好的帮手是“摇篮”,竹子编的,相当于现在的婴儿床;还有一样家什是木制“椅架”,类似于现在的学步车,只是没有滑轮,还不能跑。母亲洗衣服的时候把我们放在“摇篮”里,一只脚慢慢摇着,像催眠曲,好让我们早点睡着。“椅架”安全,做饭、喂猪放在眼皮底下就行了......
我母亲名为朱志珍,这三个字也是一辈子没有上过学的她为数不多的会写会认的字。生于1950年,她是家中的老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一家人住在溢水镇。
母亲的前半生,开头就有些悲惨的意味。我仍记得幼时,母亲经常牙疼,买不起药,总是靠偏方治。看着她喝着黄连水止疼,对我说:“黄连苦,苦不过生活。”三岁时她就没了母亲,五岁没了父亲,年幼的她天天上山打野草,为家中五口人做饭:哥哥姐姐弟弟,还有年迈的奶奶。
贯穿童年的基调是饥饿。母亲对1959年的饥荒至今记忆犹新,前一年的粮食不佳,红薯和玉米糁煮的糊糊,“干得喂猪猪都不吃”。到了1959年,正式进入了饿饭的时期,母亲每天打来野草、淘洗,加入不足一小酒杯的、连带着谷皮的碎米,煮熟,把少得可怜的米倒入弟弟的碗中。母亲甚至吃过“观音土”!母亲每次说到这里都是一度哽咽。这样的经历对母亲影响深远,直到现在看到有人浪费粮食她还会忍不住制止,有时只是一句微弱的“别糟蹋粮食,好歹能喂猪呢”,尽管城里没有人再养猪。
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母亲逐渐长大,也开始在生产队做农活、和男人一样修水库、挣工分、吃食堂。23岁那年,她经人介绍认识了父亲,从此开始了婚姻生活。
在那个饥贫交加的时代,父亲的境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父亲名为张友才,于1946年出生在竹山县麻家渡镇关东沟村,那是一个缺水的小村落。起初,父亲的奶奶去世,他的爷爷便再娶,重新组建了家庭。根据农村侄女随姑姑的习俗,父亲的新任奶奶的侄女,便嫁给了我的爷爷,生下了父亲。之后,奶奶担心当地水土过于缺水不适宜孩子成长,便搬到了娘家所在地——麻家渡镇关东沟村居住,住在一间娘家人盖的茅草屋中。小茅草屋面积不足十平方米,却住了父亲和爷爷奶奶以及小他四岁的妹妹,生活十分艰辛。父亲还记得,搬来关东沟村后,奶奶还生下过一个弟弟,小名叫爱国,却在1957年的四月病死了,无力医治,还是由当时尚稚嫩的父亲,用箩筐背着,葬在了山上。好在同年7月,又有小弟弟降临到这个家庭,略微冲淡了悲伤的气氛。小弟取名张友喜,希望给这个家庭带来一些喜乐。然而世事,并不都尽如人意。
1958年的大天旱,同样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灭顶的灾难。长时间不下雨,家里的庄稼一片颓势,爷爷便经人介绍去了离家较远的地方做活,砍柴、烧枝、肥土、开荒。家里没了当家的男人,受了不少欺负,家中那一点点省吃俭用攒下的绿豆、玉米,清水田里还剩下的一点谷子,都被人偷着瓜分了。当时的父亲尚且是个孩子,无法替他的父亲捍卫这个家庭,只能带弟弟妹妹去坡上,找来玉米芯勉强充饥。
1959年冬天,噩耗传来,说爷爷出去逃荒,饿死在了外面,连尸首都不知道葬在哪里。这时父亲只有十三岁,便成了家中最年长的男人,望着两岁的弟弟、懵懂的妹妹、垂泪的母亲,父亲知道,这个家庭,承担在他的肩头了。
在那个难熬的饥荒时期,饿死的人并不只有爷爷,而是许多许多。在生产队,父亲见了许多面黄肌瘦拼命劳作的人,死亡也是瞬间降临的事,“就像一截截树桩,突然就直直地倒下了”。
对死亡的恐惧也同样笼罩在家中。父亲承担起男子汉的责任,与奶奶一起上山打野草,为家里人想尽办法找粮食。他两岁的弟弟每天只能吃到无油无盐的水煮野草,牙齿还没长齐,只能慢慢磨着吃。这一段岁月父亲始终不能忘,以至于养成了节俭至极的习惯,尤其看不得人浪费粮食:多年后生活好起来了,一次父亲和他的弟弟吃饭,看到弟弟吃炸鱼时掐掉鱼头扔在一遍,父亲仍会不出声地凝视弟弟许久;我小时候掉米粒在桌子上,父亲也会要求我捡起来吃掉,给我讲“韩大爷”的故事,那是一个专门吃掉在桌子上的米的大爷,原型是某一部影片中的人物;父亲平时也舍不得扔饭菜,剩饭剩菜只要没坏就还是会选择热了再吃。总之,饥荒时代养成的节俭习惯,陪伴了父亲终生。
尽管想尽办法节省,但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饿死。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那一贯善良、被邻里赞为“好德行”的母亲,似乎变成了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父亲的妹妹太过于饥饿,直接用手抓着吃生产队分的谷子和生面,奶奶便将女儿狠狠打了一顿,甚至差点打算不要她;父亲的弟弟追逐时被田间的牛吓得跌落田埂,奶奶甚至没有转身去拉,只是在事后哭着对父亲说:“不知道未来哪一天我们都会饿死!”
所幸,父亲从未放弃希望,每天在山上打野草,终于让弟弟妹妹活过了那个最冷的冬天。1960年春天之后,年成逐渐变好了,但他们先前居住的小茅草屋被生产队用去做了仓库。起初他们仍然住在那,但生产队总有人担心他们会“侵犯公家财产”,就在附近的江家湾选了一块旧时用来拴马的马厩,分给父亲一家四口居住,大小只有几平方米,只容得下一张床。就这么一小块地,还有周遭许多人家觊觎,见父亲一家孤儿寡母,便更肆无忌惮地欺负。奶奶一个女子,受了不少气,父亲看在眼里,心里暗下决心:你们这些人如此不友善,等以后我能盖房子了,一定谁都不挨着!
1963年10月 6日,也许是常年受气又无人可依,奶奶患病去世了。拿着生产队给的用来盖房子的救济款,父亲决定不要房子了,把钱用来给奶奶买了棺材和白布,体面安葬了。三个孩子站在坟前,流够了无助的泪,摇摇晃晃地一夜间长大了。
没了母爱与依靠,父亲发了疯般地在生产队做工,白天做农活,夜晚也守着值夜班,拼命挣工分,以求得弟弟妹妹不缺衣食。1964年,四清运动在村里开展,这是一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起初是 “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父亲也参与其中,成了村里的代表,监督生产队搞建设、搞运动,检查是否存在贪污挪用等行为,帮忙组织生产。同年,父亲加入了中国共青团,成为了一名团员,是生产队上的积极分子,村民不愿意去的出门搞建设、开会,他都去,只是暗中担心家中的弟弟妹妹不会自己安排饮食。
父亲的机敏、勤劳、踏实、能干被村里人看在眼里。当时,公社里有一个指标,推选一名八大员(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标准员、材料员、机械员、劳务员、资料员),父亲就成了社里考虑的对象。生产队在农忙的时候想抽调父亲回去帮忙,公社干部未准许,说父亲是组织培养的对象,由此可见父亲在村里已然用品行获得了大家的认可。然而等推举指标落下来的时候,父亲却拒绝了,他认为自己没读多少书,小学都没毕业,无法胜任八大员的工作,推掉了这个机会。
但是,机会不会错过有能力的人。当又有炊事员的指标下发时,公社干部、大队长都认为父亲身体好、干活好、思想好,细心耐心,也懂得生产知识,为人也正直,便一致推举了他。1971年5月20日,父亲被调到竹山县溢水区财税银管理所任炊事员。同年7月1日,开始正式拿工资,每月27元,还有口粮38斤,成了国家单位的一份子。五年后,父亲因表现优异,又被调到竹山县财政局做炊事员,正式进城。这期间,母亲独自带着我和弟弟留居老家麻家渡镇,种地务农,直到1986年8月,父亲终于将我们娘母仨的户口转到城里,一家人得以团聚,而在此前分居两地的十多年里,父亲和母亲只在一起过了四个春节。
进城后,母亲凭借勤劳能干、做事麻利的优点,在纺织厂找到了纺线绳织袜子的工作,一做就是数十年;我和弟弟得以在城里上学,我也会在假期时去针织厂帮忙打工,补贴家里,一家人的日子逐渐好了起来。
2002年,在财政局的食堂操劳了一辈子的父亲退休了。他穿着整洁的中山装,夹杂着银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财政局的职工看到他都会礼貌地叫一声“张师傅”,他也微笑颔首,此后过上了休闲的退休生活:带带孙子,享尽天伦之乐;与老朋友晒太阳、打牌、闲聊,与母亲一起绕着小城散步;订阅了杂志《老同志之友》,时常戴着老花镜阅读;偶尔回去参加财政局退休干部的活动,生活也算惬意。他常常说:“我这是得了共产党的利,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呀!”
坚强的母亲在2002年企业厂垮人散后,依旧是打小工贴补家用,直到赶上国家对企业下岗人员的补贴政策出台,我们给母亲买了“五七工”,2011年11月,整整满了60岁的母亲领到了第一个月561元养老金的时候,母亲孩子般嚎啕大哭,嘴里念叨不停:感谢国家,感谢党,让她也成了有退休金的人!如今72岁的母亲每个月有1847元养老金,每天都是笑眯眯的。
母亲与父亲勤劳、踏实、节俭的品质,对弟弟和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有过苦痛的岁月,有过难捱的日子,但还是常对我们微微一笑:“我们,生活还是不错的吧?”
(作者单位:竹山县财政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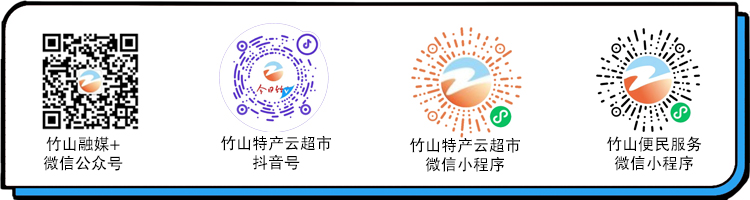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