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春耕
打记事起,老屋都在,四十年来一直发生着变化,不断地丰富着我的记忆,绵延着悠长而又温馨的亲情故事,细数起来,总是那么的甜蜜。
老屋坐落于山脚下一方僻静的村湾里,四面环山,围成一个口字形的小盆地,面积仅有百十来平方米,可是在我们这群后辈的世界里却是一方温馨的港湾。在父亲的眼中,老屋是他一生的家业,承载了他一生的辛苦打拼,是他作为一家之主的见证,尤其是三次建房、修房的经历,已经深深定格在他和母亲的记忆中。
据母亲讲,建家之初,他和父亲只继承了半间土墙小瓦屋,这间土屋只有十几平方米,厨房、寝室、堂屋连在一起。四十年前,有这么一间房也算是比较奢侈了。因为爷爷早逝,父亲作为长子,只能分得一小间,两位叔叔还得由奶奶拉扯长大至成家立业,在如此情势下,父亲必须建房才能满足正常的生活所需。
在我六七岁时,依稀记得父亲建过一次房。那时建房的场景煞是热闹,动工时家里请了很多工匠,都是和父亲一起在外做副业的小伙子,个个都力大无比。有木匠一人,下墙脚的三四人,挖土的四五人,挑土的七八人,打杵的两三人,整个建房过程从头至尾最快也得几个月。因为每一阶段的基础工作都需要考虑到时间和气候的因素,实在急不得,太急建造的房屋就不够牢固。在我的印象中最热闹的建房场景要数筑墙。十几个工匠聚在一起,挖土的挥舞着锄头用力地向黄泥地掘去,三两下土筐就被装满,干的劲头十足、满头大汗;挑土的力大如牛,扁担都压弯了也不肯歇息,伴着吱呀吱呀响声,一路大步流星地冲向搭在墙头的木桥,源源不断地将黄泥土运向墙头;倒土的人接过装满土的筐子,“嗖”的一声倒进墙板;打杵的师傅马上撸起袖子,手握墙杵咣咣有声,不停地向泥土捣去,一阵闷响过后,一墙板土便已打完。打杵的师傅取出墙板,拍墙的工匠马上轮起长柄的拍叭儿,一阵叭叭脆响,平滑整齐的墙面便建成了。每当见到这个场面,我和小伙伴们总是兴奋无比,因为这是最动听的劳动乐章,太有趣了。
打好土墙后,要数架盖椽木檩料了。建房的木头由树木变为建材要历经曲折。据父亲讲,老家房顶上的每一根屋檩都是它从离家5里之遥的大山用肩膀一步步扛回来的。能作房檩的树木必须是笔直的枞树。一丈多长的枞树,从丛林砍下时,少说也有六七百斤,必须乘湿去枝刮皮待晾干后一个人才能扛走。一间房需要的木料大概要百十来根,可以想象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才能把它架上屋顶。房屋中作为门方、门顶板的木料必须是上好的坚固耐用的木材。家里堂屋的门顶板是父亲从九华山林场中买回来的,连门扇窗户皆有据可考,有来自官渡的,有来自茅塔的,还有来自县城木材的,最远的还有父亲从南漳县在河里放排时贩回的木料。
建房的最后一道工序要数盖瓦,泥瓦从窑匠师傅处出窑后买主要事先打听定购才能买到上好的瓦片,因为当时多是手工作坊生产,产量有限。父亲是在泥墙建好前就张罗着打听购买泥瓦的。购买交易谈妥后,随即用竹篓挑回来,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一篓一篓逐一安放在院子里僻静的角落,摆成一个规则的圆形,层层叠叠很是好看,坐在上面硬中透凉挺好玩儿,父亲特别叮嘱我们这群孩子不要上去乱踩,踩坏了瓦盖在房上就会漏雨。最有意思的莫过于传瓦上房。那时没有吊车,必须先把瓦运上房顶的椽子上,然后再由师傅一匹匹的盖严实。从院子里腾瓦的场地到屋顶大概有二三十米的距离,只能靠人工接力才能把瓦快速地运到房顶。当时哪家能建间房在村里是天大的喜事,而在建房中小孩子唯一能帮上忙的就是传瓦了。传瓦时一般是全院里男女老少一齐上,如果距离远就需要更多的人手,我们这群小孩子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一次传三匹瓦较为合适,有时传瓦时间长,不小心碰破了手指头,仍然强忍着疼痛快乐地享受着传瓦的喜悦。总之,建房是我们这群孩子渴望享受的快乐,因为院里有人建房就一定要办酒席,办酒席就有好东西吃,而且开工完工之时还免不了要放上一挂鞭炮,我们捡到未燃放的鞭炮又能享受到更大的快乐,自然有种莫大的吸引力。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对房屋又进行了一次维修。那时大哥和父亲一起在外搞建筑,学会了砌匠的手艺活儿,据说这门手艺当时很挣钱。暑假期间,父亲萌发了把老屋外墙粉刷一遍的念头。说干就干,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到老家一个名叫狮子口的山脚下挖了一种叫作白山土的泥,运回家把泥用竹筛筛成细细的粉末,再挑来水,和泥拌和在一起,然后吩咐我们兄妹几人卷起裤子在里面不停地踩,说这样才能将粉墙的泥料伴和均匀。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兴奋地踩着泥,一双小脚丫浸在黏稠的泥浆里、凉凉的、滑滑的、糙糙的,感觉好享受。和好泥后父亲和大哥便搭起木梯抹起墙来,刮泥刀从上到下,从左至右,所到之处刀刀入墙,如同贴饼般服帖平整。忙活七八天之后,四间屋的墙壁从上至下,黄里透白,煞是好看。要知道在那个还没有石灰做装修材料的年代,村里只有我们一家粉了白山土的墙,那种自豪之情自不必说。
2017年,已是父亲85岁高龄,正值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全面铺开,村里很多破旧的土墙房经过穿衣戴帽换大瓦之后焕然一新。我家不是扶贫户,见到邻家的房屋旧貌变新颜,父亲心事重重,经常在我们的耳边吹风要修房,因为没有积蓄,父亲只能不停地叹息。我们兄妹几人一合计,大家齐心协力出资凑了2万元实现了父亲的愿望。当我们把修房的专款交到父亲手上的那一刻,老父亲简直乐开了花,立即张罗起修房。因为老屋已历经30个春秋,很多木料都已坏掉,除开墙体不换之外,原先的材料要全部换掉。二哥买木料、三哥买瓦、大哥具体组织施工,父亲则全面指挥,母亲和嫂嫂在厨房张罗工匠们的生活,我虽然没做什么也是团团转,整个忙碌的场景简直是热火朝天。半个月后一个全新的老屋终于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墙体一溜儿白,屋瓦一溜儿黑,房脊还造出腾龙的造型儿,够威武气派了!好马还得配好鞍,父亲将入户门也改成了大气的铝合金朱门,还用上了自来水和冲洗式厕所,不久又安上了宽带,看上了有线电视......父亲在他八十多岁还能再干一次修房的伟大使命,幸福之情自然无与伦比。这次大修老屋,在父母的心中是值得庆贺的事情,母亲经常感叹,如此好的时代再回去三十年该有多好。
岁月流逝,不知不觉间,我由无知的少年步入中年,有了自己的小家。每当乐享小家幸福之时,仍然难以忘记远在故乡的老屋。父亲年至九十岁,仍然固守在他一生传奇的老屋。2020年,尽管母亲已经远去,我们依然像铭记老屋的经历一样常常忆起关于她的幸福。
青山不改,老屋犹在,亲情永续。
(作者单位:竹山县特殊教育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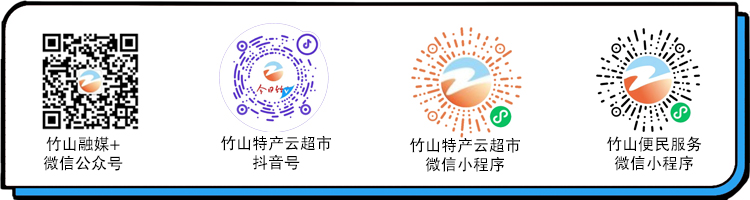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