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情一段文字,不如钟情一个故事;留恋一处风景,缘于风景深处的背影。《堵河文艺》几乎与我同龄,风风雨雨几十载,云烟历史,沧海一粟,与她的正缘,能够回味和讲述的东西虽然不多,但足够。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官渡读中学。学校是解放初期的老式四合院,院子每个角落都有一棵擎天的白蜡树。清晨,泛红(电压不稳)的亮光从木格纸窗透出,映照着读书人的小脑袋,灯一亮,琅琅书声顷刻间在院子回荡。秋天,白蜡树叶儿四处纷飞,小石子路面被铺成一条灰白相间的毯子,静静地,还可以听到秋虫在里面打滚儿的声音。冬天,白雪覆盖校园,垫着厚厚的积雪,我们几个人合力摇落白蜡树树枝上的雪花,飘飘洒洒,如梦如幻。这样一群孩子,踩着落叶舞着雪花,慢慢长大。忽然有一天,校园四合院的景色被一个邵姓同学描摹得如诗如画。《家乡的冬天》,500字不到的一篇散文,在《堵河文艺》上刊发了。校园沸腾了,一个13岁小男孩第一次真实而形象地诗化了我身边的景致,那么美丽,那么迷人。它不像课本里的文字那样遥远冰冷,也不夹带历史的尘烟。语文老师叶康玉捧着它,在全班朗读,在全校朗读。同学们争相模仿,纷纷赞美家乡和校园的四季,当然,也包括我,然,无一成功者。初识《堵河文艺》,就这样擦肩而过。
当时,我就在想,这《堵河文艺》从哪儿来的?如何才能拥有它,成为它的读者或作者?可惜,我没有找到答案。
初恋时,车马都慢,时间就像蜗牛,难得一见诗和远方。1991年,一个手抄本落到我手中。随便打开它,爱,花瓣雨一般向我飞来。“分离的痛苦早已湮埋在我的记忆深处,唯有相爱的甜蜜与遗憾,我却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就像咀嚼着一枝不太成熟的橄榄,有清香,也有苦涩,令我愁肠百结,回味无穷。”这是谁的爱情?这么贴近我的心。我向手抄本的主人(同事)刨根问底,原来,这是他从《堵河文艺》杂志摘抄下来的。我立刻索来了1991年第4期《堵河文艺》,解我千愁。杂志办得真好,开篇便是长篇报告文学《燃烧的青春》,记竹山县壮烈牺牲的税务专管员范全利,看得我热血沸腾。我找到了手抄本里那段话的出处—《爱的离心力》,作者彬彬。这是一个革命军人的爱情故事,从校园到军营,爱情像潮水一般涨落,四季考验着天各一方的两颗心灵。纯洁的爱情无处不在,但精神匮乏时,其光更亮。洋洋洒洒几千字,连标点符号都充满了笔墨的清香,我愈发觉得这《堵河文艺》离我更近了,而这几句鸡汤也被我保存至今。
1997年,《堵河文艺》复刊,更名《堵河》,由我的中学老师华赋桂主编。本期,华老师亲自操刀的文化散论《堵河地域特色文化探源》,令人印象深刻。其语言风格颇似鲁迅,犀利、深刻,亦有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雄奇,荡气回肠。散论纵横几千年,思接几万里,把堵河文化像剥笋子一样,代代剖析,层层解读,其文采、其学问到今天也令我这个学生难望其项背。
2007年,我到柳林从事变电运维工作。柳林山大,交通不方便,很寂寞。我就在竹山论坛上写豆腐块儿,喧嚣发泄孤独和无聊。也许是环境使然,清静之下,竟然思绪如潮,几年下来,我累计写了20多万字,这些文字随心所欲,无章无法。童年、故乡、恋爱、书籍、歌曲、路人等都被我写了进去。2008年,邮箱里收到一封来自武汉的信,是《堵河文艺》老编辑、作家罗维扬发来的。信中,他说在今日竹山网上发现了我的文字,觉得还行,并选择性地进行了点评。这信让我激动了好久,我盲人摸象式的写作结束了。
2011年,在罗维扬等很多人的帮助下,我出版了散文集《竹山的幸福》,梦圆文学。后来,从罗维扬老师的回忆录中,我大致理出了《堵河文艺》成长史。
《堵河文艺》大约创办于1972年,开始是蜡板和油印后装订成册发行,以“写中心,唱中心”为传播材料。我听父亲说起过油印的《堵河文艺》,一股油墨味儿,但传阅度高。1974年夏至1984年十年间,罗维扬主编《堵河文艺》。罗老师把它改为铅印,32开,64页码,季刊,不再以说唱为主,而是向综合性文艺刊物方向发展,兼容并蓄。当时,吸引了很多专业作家,也培养了相当数量的业余作者。这十年时间是《堵河文艺》的黄金时代。罗维扬调离竹山后,陈新民、黄成勇、华赋桂等人接棒《堵河文艺》,但因种种原因,刊物几起几落。
2010年,《堵河文艺》老编辑罗维扬从武汉回到竹山,在上庸独居时,倾靠十堰广播电视报,于2013年创办过文学刊物《笋》,其办刊宗旨是“打捞中国好文字”,比肩《武当风》。时竹山论坛正青春,罗老师随手就拣来了竹山好文字。兴趣所致,王素冰的《远去的背影》,真如酱香陈酿,回味悠长。从1940年开始,王家大院里弟兄六个,在烽火与贫瘠中,投影出他们或豪放或悲伤或卑琐的人生故事。若干年后,这些故事被一个有着悲悯情怀的后代子孙,演绎成跌宕起伏的平民传奇。莫言说,故乡是每个人绕不开的存在,概无例外。省作协会员袁斌的《从庸字看庸国》则另辟蹊径。一个“庸”字,他硬是掰出了诗、歌、政治、建筑、音乐、地理等万千气象,且收放自如,这金刚钻实在了得,我长了知识,也开了眼界。后来,《笋》还是夭折了,原因不详。《笋》是罗维扬之于故乡的表达方式,也是堵河文艺史册里的孤本,我很珍惜。
只要堵河不断流,堵河的文脉就绵延不止。回归初心,需要热忱,也需要创新,当然,更离不开人民币。2016年,沐浴时代春风,全新《堵河》悄无声息地上线了,彩印、双月刊、16开、100多页,比以往任何一期都精美,这是多少竹山人的期盼啊!新晋主编王素冰先生给我打电话约稿,成就感油然而生,天命之年的我,终于从读者变成了作者。捧着崭新的、厚厚的《堵河》,我爱不释手,我像迷路的孩子找到了妈妈,像情人再次相见。堵河水总是这样深情,她以母亲的胸怀拥抱每一个漂泊的儿女。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堵河》复刊以来,团结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从50后到00后,老凤新雏花开满园。只要有空,我就翻一哈儿《堵河》,找一找古人读书时的青灯滋味,沉浸在故事与情感当中时,我像是约会一个多年的朋友,又像是迎接夏天吹过来的一丝清风,内心很安宁,神情也很愉悦。社会在发展,人们的阅读方式在变,读者获取养分的渠道也多,难得《堵河》还坚守在传统阵地上。所以,首先要感谢母亲河堵河,是她触发了文学人的灵感,并赋予他们写作的土壤,也为广大读者带来了持久的人文气息。感谢我们的党和政府,为《堵河》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支持,文学和艺术一样,是需要金钱来体现价值的。还要感谢一代又一代的领导和编辑老师,像徐纯孝、罗维扬、唐明文、陈新民、袁胜敏等,他们从青丝熬成白发,才使得《堵河》这股清流润物无声、汩汩向前。
闺蜜80岁的老母亲去世了,殡仪馆里,她轻声讲述着母亲的生前点滴,一个小细节很是打动我。她说,母亲生前是退休教师,《堵河》是每期必看,遇到好词好句,母亲总是先用笔画上记号,然后给她打电话,要她认真阅读这些字句,过一段时间还要她说些心得。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堵河》是不是和女儿一样,成为母亲最亲的陪伴?
《堵河》复刊后,定期不定期搞笔会或者开讲,很荣幸,每次入会,都能发现新面孔,真好!他们是《堵河》的未来和希望。英国人罗素说,支撑我们人生的动力是三种单纯而又强烈的感情,它们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我始终认为,它不仅是普通人生活的动力,也是我们写作者写作的出发点和基调。每个喜欢文字的朋友,潜意识里一定布满这些敏感神经元。我十分愿意把它分享给年轻的文友,希望他们像当初的我们一样,守住那盏青灯,以梦为马,表白他们独一无二的风流与荒凉,深深地祝福他们!
对于《堵河》,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它让我想起一位网友,宝丰镇的张世红。竹山论坛正活跃时,每隔一些时日,都能在论坛上读到他的小说或散文,语言很优美。跟着他的小说,我曾学会了一个成语:结草衔环。张世红出身寒门,对于文字却有着与生俱来的执着。当时,他一边打工,一边寻找精神的阳光,或许是世事消磨,后来,他的文字跟时光一起,没了下文。《堵河》复刊,不知道他知道否,也不知道他向《堵河》投过稿没,那可是他的夙愿啊。其实,人在他乡,能够平安,鸿儒往来,有空了喝酒品茶,闹中取静,不负一段文学人生路,也挺好的。
燕子走了,还有飞回来的时候。时序深秋,薄念,唯念《堵河》,唯念青涩。(若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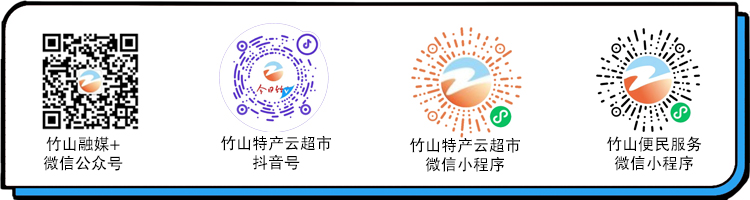


















请输入验证码